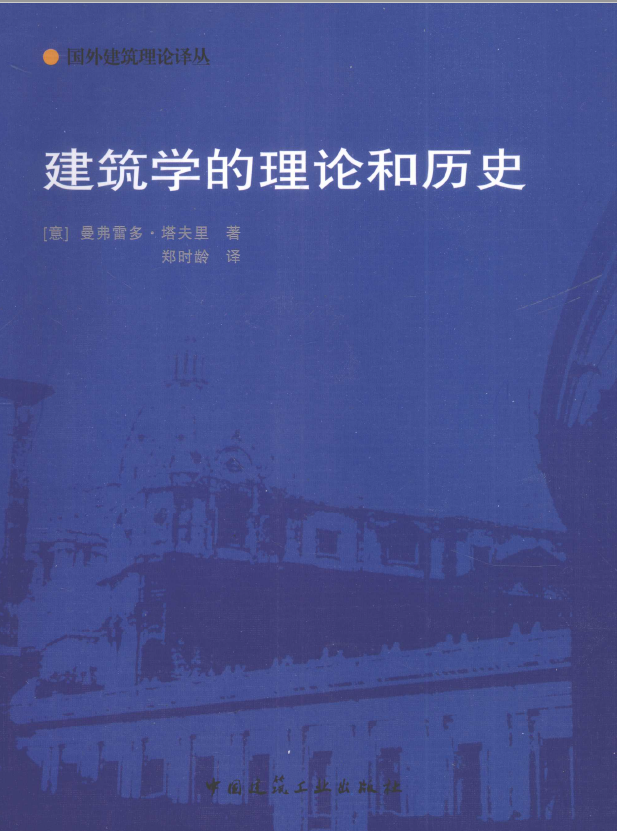很多人会说中国传统建筑是如何与自然协调,这其实特别泛泛。宋代的建筑,最精彩的是它跟山水的对话能做到精确对位——不是协调关系,是互相补位、互相映衬的对话关系,这是种不一样的生动。 王澍 Wangshu 从生物学上讲,我们先倾向于喜欢具有显著自然特征的景象。 罗杰·乌尔里希 那些早期的家完全是由自然元素组成的:它们这些场所可以遮风避雨、有可以食用的绿色植物,适于耕作,有水,有狩猎者和猎物,有季节变换,有阳光和风暴。 研究表明监狱里那些可以看到自然景观的房间中罪犯比没有这个环境的房间里的人犯病的机率要低。其他的研究也表明给生病的人送鲜花的传统可以提高他们的康复率。 材料的变化并不一定会改变它所传达的信息。19世纪的些作家提出,哥特式建筑是对树林的一种模仿﹔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解释过于天真,但是对于观看的人来说的确会有类似的效果。例如韦尔斯的牧师会礼堂,或者埃克塞特中殿里装饰着棕榈叶的拱顶,能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林间空地的感觉,我们很容易在这两个与某种原型相一致的建筑中找到愉悦的感觉。为了再一次改变材料,东京建筑师坂本一成最近在伞形钢柱上做了一系列波浪形钢屋顶。1988年的藤冈住宅是这个系列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它那非常抽象的室内设计看上去就像是树的枝叉一样。 因此,它证实了我们喜欢被自然环境或者它们的替代品所环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环境都能带来安静的感觉。文学作品中对密实的自然环境的描绘往往会给读者造成焦虑不安的感觉;今天当我们想像被留在曾经是我们远古家园的非洲热带雨林中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恐惧和害怕。...
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很好的生存机会,我们就必须在四种基本行为上具有很高的竞争力。摄取营养、繁殖后代、居住安全以及勇于探索。 从广义上来说,适当的居住就是建筑的全部。 格朗特·希尔德布兰德 Grant Hildebrand《建筑愉悦的起源》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 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 伯鲁乃列斯基在建立语言记号和符号体系时,与伟大的古典范例进行超越历史的对比。出现了第一次伟大的探索,试图使历史价值现实化,将神话时代变成当今的时代,使古代的意义成为变革的信息,将古代的“言语”( parole)转换为普遍的行为。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伯鲁乃列斯基的成就并没有在建筑设计史上导致彻底的变革,其根本意义在于他的非历史化。理解这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是15世纪迄今这个历史时期内建筑理论的决定性因素。 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伯鲁乃列斯基是第一个被单独立传的文艺复兴艺术家。这是文艺复兴称颂个人功绩的最初预示,同时,建筑史也开始转型为个人成就的历史,而不再只是罗列一系列无名的纪念性建筑。 伯鲁乃列斯基同时代的人,在他的建筑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新颖的东西,他们把这种新潮归功于古代,但他们对古代却知之甚少。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罗马风的地方传统和14世纪晚期的建筑,以及基督教早期、拜占庭和地中海东部的中世纪世界的建筑,还有古罗马的废墟中,找到伯鲁乃列斯基建筑的原型。...
尤为重要的是应当指出,无论是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原来的词义、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波普艺术的极端反人文主义或是路易斯·康和他的追随者对新客观性的追索,都坚持同样的理想境界,如果不致引起自相矛盾的论争的话,我们会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我们发现这种理想境界完全建立在反历史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基础上,令人担忧而困惑。如果我们想继续前进,深入现象的本质,不愿为不完善的意识形态所左右,那么我们就不会如此不安了。 欧洲先锋派运动在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不就是一场对历史的真正挑战吗?现代艺术难道不只是企图摧毁历史,甚至也摧毁作为历史产物的现代艺术本身吗?如果从这一非常特殊的观点来看,达达派和风格派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对立。 问题不仅如此,路易斯·康已陷入历史提供的素材中,并且过分地使建筑设计非历史化。另一方面,他的新造型主义神秘观试图以救世主式的调解来消弭矛盾和悲剧。如果我们把萨尔克学院生物研究实验和施罗德宅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路易斯·康的思想体系与新造型主义神秘观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显著。 因此,传统观念中的先锋派反历史主义在超越反历史主义的过程中得到证实,其原因即在于此。巴尔特认为:“神话是反历史的”,如果真是如此,而且神话的欺骗性在于把人为的因素(意识形态的人为性)用“自然”的假面具来遮掩。这正是以新的神话为借口,回避现实的大好时机。受现实约束,就不可能成为时尚和神话,甚至不可能转化为面目一新、严谨而同时充满活力的探索。这样一类探索的目的应当是系统并客观地理解世界、事物、历史和人类习俗。 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
建筑风格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 当建筑师谈论风格,意味着什么? 风格是建筑师创造的一种意识形态,来占据设计的绝对主导权。 把人为的意识形态用宏大的叙事结构伪装起来。 被统治的群体,没有完整的意识形态。 掩饰性,风格没办法说清楚,自身矛盾性。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在今天已不再是新鲜的事物,它们已广泛应用于建筑研究。我们可以立即指明它们在设计分析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它们为建筑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它也是这一令人焦虑不安而又变幻莫测时代的客观需要。其次,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任务,目的在于认识那些形成苦恼而又危机四伏的观念体系的现象。这些观念体系正由于日益衰落而变得不可捉摸,失去了它们的意义。 不愿沉溺于徒劳无益的哀诉的批评必须从事基础分析。作为分析方法———一旦意识到这点,而不是作为赶时髦的学说-——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就显示了它们的积极意义。 然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也同时显示了危险性,其思想体系掩饰在显然迟疑不前的观念背后。因此,批评应在有依据的历史主义范围内选择并传达它所获得的素材。 如果真像弗朗索瓦·菲雷(Frangois Furet,1927-1997年)所说的那样,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08-2009)的结构主义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于“历史上,人作为客体的结构主义观点渐渐直接取代了人作为上帝的观点。”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大多数现代艺术已经预见到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达达派、风格派和苏俄构成主义的某些观点到勒·柯布西耶身上都能发现这一变化。当然不能就此断言它意味着人本位论的终结。在这些艺术流派看来,人类相对于他所创造的世界有着新的也更为真实的地位。 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建筑是否一定存在于不断变化的历史当中? 建筑是否需要不断进步,不断改变? 康德式的先验视角 我们不想要新的建筑式样……但是我们想要某种式样……我们有一个旧式或新式建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真正能被称为建筑的建筑。 在我看来,在今天的大多数建筑师中间有一种对原创性( Originality)的奇妙误解。原创性的表达并不依赖新词汇的创造……一个有天赋的人可以采用任何当前的风格并加以使用……我并不是说他不能挣脱材料或规则的束缚……而是这些自由应该像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使用语言的自由,而不是为了特立独行无视各种规则。 约翰·拉斯金 John...
阿道夫·路斯 Adolf Loos(1870-1933) 尽管如此︱阿道夫·路斯1900-1930年文集 或许对德国人来讲,听到说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文化而采用英国的文·化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保加利亚人也不会爱听这个,更不用说中国人了。感情用事在这儿不起作用。对于一些稀里糊涂的人,创建国家风格的呼声落到了服饰、床上用品和夜壶等古怪的方向上。但讲到枪械则是英国样式所向披靡。 对此,德国人能够自我安慰地认为,19世纪英国人强加给世界的是德国人自已的文化。日耳曼文化在不列颠诸岛上完整地保留下来,如同覆盖在苔原冰雪下的猛犸象,如今,重焕活力生机勃勃,正践踏着所有其他文化。在20世纪,将只会有一种文化统领全球。 古时候许多文化能和睦共存。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文化的种类不断减少。在15世纪,日耳曼人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并被迫接受了拉丁文化。拉丁文化曾一统整个欧洲直到19世纪。十年前我曾试图描述这两种文化的异同:拉丁文化,是猫的文化;日耳曼文化,是猪的文化。 猪是日耳曼人最主要的驯养动物。它是动物中最干净的,正如同德意志人是欧洲人中最干净的。它也是依赖水的动物。它如此急需用水,因为它必须半天就洗一次澡。干净这一抽象概念应该对任何动物来说都是陌生的,但猪的皮肤渴求湿润。拉丁人和东方人对此无法理解。因此,在他们那儿,猪的地位十分低下而且还被逼——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折磨——在自己的污秽物中进食。犹太人认为它的肉不洁。但在德意志农民那里,猪睡在家里。在所有动物中,猪是最不可舍弃的。它和人一样裸露皮肤。在不允许在人类尸体上操作之前,解剖学家们是在猪的身上研习解剖技术的。 但正如我说过的,拉丁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猪先弄脏了自己,才要水洗。拉丁文化中有一个谏言说的正是:不要弄脏自己,如此就不需要水来清洗。如果一个德国父亲告诉自己的儿子:“需要每天洗澡的人肯定是个肮脏的讨厌鬼。”这个德国父亲应该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
阿道夫·路斯 Adolf Loos(1870-1933) 尽管如此︱阿道夫·路斯1900-1930年文集 在过去几年中,报纸杂志的作者都试着让我们鼓起勇气面对现代艺术家毫无品位的作品。我现在试着让你们鼓起勇气面对自己没有鉴赏能力的情况。 想学击剑的人必须自己手持轻剑。没有人只凭着观看就能学会击剑。 同样,任何想打造一个家的人都得自己亲力亲为,否则他将永远学不会。 这个家可能到处都是错误,但它们都是你们自己的错误。在约束自我和摈弃虚华之后,你们会很快意识到这些错误。你们会更正它们并进步。 你们的家随着你们形成,你们也会随着你们的家成长。...
01 斗争不是为了杀死装饰,是让它从“美丽的”变成“平庸的”。 02 “如果我像你一样对骑术、马匹、皮革,还有马鞍一无所知,我也会有和你一样的想象力!” 03 只有你们自己能布置你们的家,因为首先只有这样做,它才能真正成为你们的家。如果让别人,不管是画家还是室内装饰师来布置,那它就不是一个家。它顶多只能算一系列酒店房间,或者是对一间住所的嘲弄。 04 他们只是贩卖艺术吗?不,他们出卖艺术。...
2021年7月24日,空调温度有点太低 第一段梦充满了情色的碎片,但没有质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理状态,一种不用言说的语言,莫非是把自己分身了,然后后自己与自己调情? 第二段梦是从一个到另一个地方,骑着一辆不锈钢的摩托车,车头有一个喷头,速度越快水喷得越远。停好车,上楼,房子里有一个超大的蒸笼,揭开盖子,只有一个小碗米饭放在里面。被使唤下楼去拿酒,走到楼下,是一个中学,好多人,但是我光着膀子没有穿衣服,找了好几处才找到放东西的地方,发现被偷走了。然后上楼,楼梯不是均匀的踏步,是一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台地,我像个猴子一样,很轻松地蹦上去了。 2021年6月22日 醒来后时只记得一个场景:梦里回头忘了一眼,处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地面是粗糙的石头,边缘处有一个楼梯,远处是天海相接的地方。 2021年4月20号,凌晨,雨停,有鸟叫 准备把一些杂物放到仓库,下了电梯就直接到了,仓库在一个天桥下,没有墙,也没有顶,地上只有一把锁,有一个大妈路过,说要留出消防通道。 突然来了一个丧葬队,路很窄,奔跑,躲避,闯进了一个园子,顺着廊子走,尽头是一个寺庙,匆忙烧了香,侧门出。...
00 能在承前启后的时代保持清醒的人不多,路斯算一个。 01 关于欲望 给路斯贴任何禁欲主义的标签都是不合适的。在路斯眼中,人类的欲望是有限且宝贵的,人类永远需要鲜活的欲望,才能产生当代的第九交响乐和当代的纯粹理性批判。因此,沉迷于那些过期的欲望就是罪恶。 02 关于区分 路斯认为“实用艺术”是一个倒退的概念。把艺术、手工艺、科学……这些明确分开,才是进步。他预言了建筑做为一个整体的破碎路斯一定会认同后来有的叫库哈斯的人,一种如果路斯听到今天的人们还在说“建筑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之类的屁话,一定会气得吐血。...
阿道夫·路斯 Adolf Loos(1870-1933) 尽管如此︱阿道夫·路斯1900-1930年文集 有人指责我在上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背离了我的立场,指责我 不忠于自己。二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宣传艺术和手工艺之间的差异,不允许 任何一种艺术手工艺或应用艺术的概念存在,违抗着所有的同时代的人。 我写道:“或许人们想说明服装产品会变化,并以此贬低它们?那么 就有必要用同样的标准看待艺术作品了。”让我们看看我是否在此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