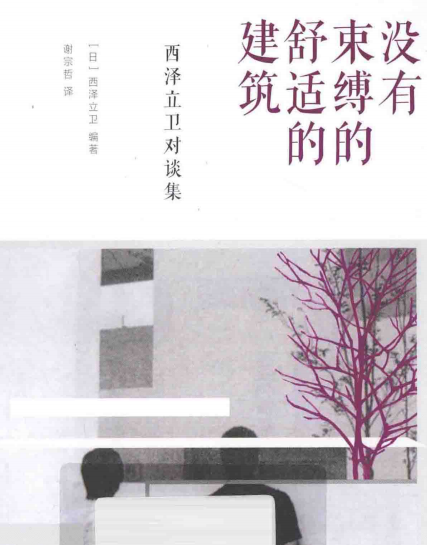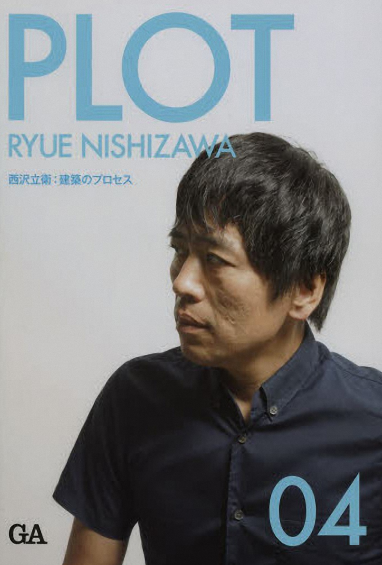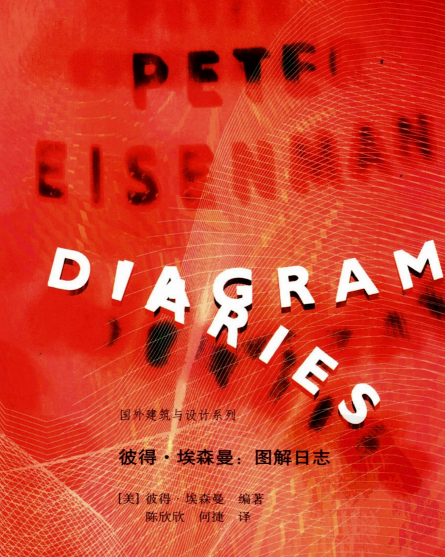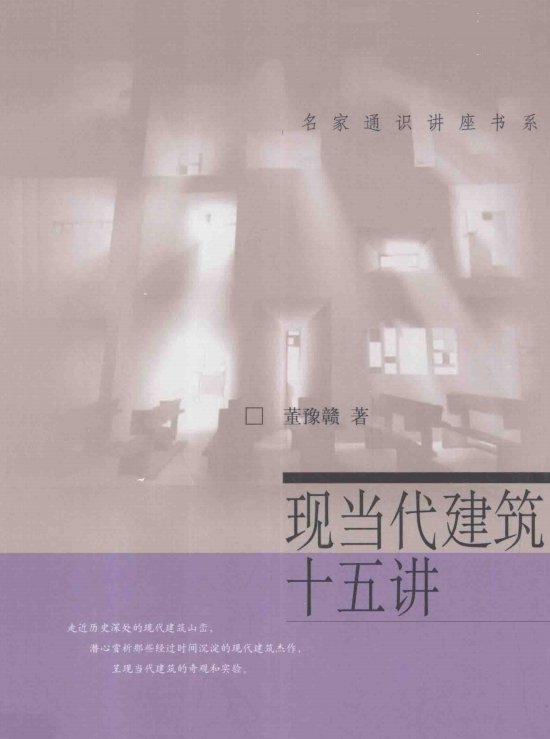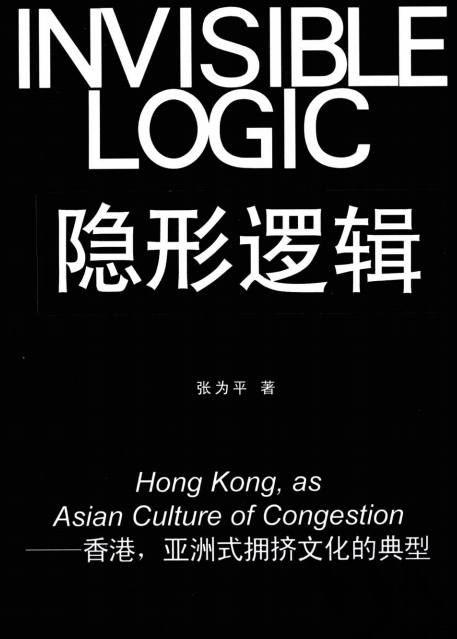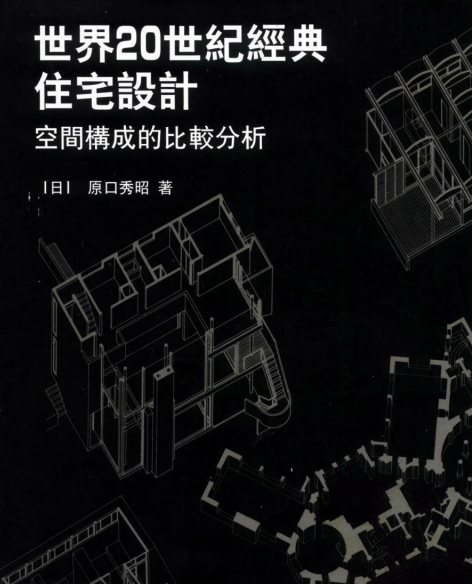现在的建筑界当中,所谓的环境问题对策,是类似像屋顶绿化、或是加上太阳能光电板这类对症疗法般的东西。这样的做法使得建筑物越来越复杂化、重装备化,于是建筑只能越来越丑。感觉上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建筑业界除了提出丑陋的答案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我真的认为肯定是会有更简单而美丽的、直接的答案的,不是吗? 关于无障碍的问题我也感觉到了相同的事态。无障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明明就是个无论男女老幼,还是坐轮椅的人、撑拐杖的人、小孩子等大家都应该能够在一起的那种任谁都会有同感而毫无疑问的简单问题,但试着去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时,建筑设计这边就做了一大堆类似装上密码锁、装两只手扶梯、造出各种厕所并且加上声音装置等等,不断重复地进行增改,似乎只有做出类似法兰克博士所作的科学怪人般的那种缝缝补补式的建筑的解答。我认为之所以会说除了这种对症疗法以外没有任何解决对策,在于我们对该问题完全没有vision(远见)的缘故。不过,不管是环境问题还是无障碍的问题,在最根本的问题上都是单纯的,感觉上只要改变价值观,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一举简单地加以解决。我认为现在是大家都终于想要朝这个方向来做,但又为此感到痛苦的时代。 在环境问题中所想的,是能够和西洋的东西对抗的、绝无仅有的好机会吧(笑)。例如和欧洲人在一起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困惑的是,他们在呼吸了干冷的空气时会说那是很新鲜( fresh)的。温暖而潮湿的空气就不会用fresh来形容。也就是说,干燥的( dry )空气是最清净而新鲜、干燥的环境是最舒适的,而温润潮湿的暖气则为不洁的,这样的想法是他们的价值观。我们在夏天会开冷气或许也是顺应着那样的价值观吧,不过因为亚洲有许多地方高温多湿的缘故,有不一样的气候与文化,例如在泰国、台湾与日本所生活着的亚洲人,感觉上会具备连wet也是可以舒适的感受性噢。在夏天的午后,夕阳就那样慢慢地落下,就在一种温润的气氛下,虽然满身大汗说着“好热、好热”,但一边喝着啤酒的瞬间能感受到一种舒适(笑)。 所谓的环境问题,我认为是我们的价值观会共同产生的部分。因为那是人类与自然直接接触的部分。从这样的地方来思考空间的模型我认为也会是一条可行的路。 西泽立卫 Nishizawa...
就建筑的做法而言,西泽先生的House A虽然是以杆件式的结构所构成,但是从外侧来看却像是个盒子。我认为整个控制的处理可以说是半吊子的,对于这件事我也曾对西泽先生说过很多次。然而,后来我却发觉这个既非箱形也非构架式的空间并不是半吊子的东西,这个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妹岛和世 Kazuyo Sejima
现代主义发轫以来,建筑设计是要给世界一张中性的脸,无关乎表现,其目的是生产客观而非主观的建筑。但事实是:不管建筑该多么中性,没有一栋建筑是客观的。勒·柯布西耶或许会坚持:“房子是居住的机器。”但就算住在一栋最忠于极限主义、全白的顶楼,那仍然是个性的一种表现,因此不算中性的空间。 有些人认为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柏林新国家美术馆是有史以来最客观的建筑,这栋玻璃幕墙建筑终结了所有的玻璃幕墙建筑——只有平坦、黝黑的屋顶、八根柱子、玻璃构成的立面。没有传达任何信息,对吧?它的空无一物挑衅我们,无所遁逃。这是我看过最有侵略性的建筑之一。 丹尼尔·李布斯金 Daniel Libeskind
董豫赣. (2014). 现当代建筑十五讲. 第一讲 建筑与文学: 大建筑的衰亡 建筑的发端/建筑的象征/建筑的风格/大建筑的辉煌/作为特殊时空的《巴黎圣母院》/建筑是凝固的史诗/作为巴别塔的建筑术/圣经会摧毁宗教/印刷术将杀死建筑术/这些会摧毁那些/文学将杀死建筑/小将杀死大 第二讲...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以符号语义学为模式的城市设计承认在城市中同时存在着各种主导性的社会价值结构的话语,它们互相交织成复杂的本文,盲目迷信科学技术一种价值结构话语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这并不成其为与科学技术世界割裂的理由。回想一下福柯的论断: 当代一些人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活动……指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存方式,直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是同一个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们就与科学和技术领域一样,依存于同样的范畴。
原口秀昭 Hideaki Haraguchi. (1997/1994)世界20世纪经典住宅设计:空间构成的比较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0th-Century Houses...
抹灰。 萨伏伊别墅,砖混抹灰。 让轻的东西表现出重量感。 拉图雷特修道院,预算有限,部分抹灰。全混凝土错觉。方糖,极度封闭的情况下,表现轻,如同朗香教堂。 康为什么要用重的材料来表现轻。 去物质性。 独石。 多米诺,无梁楼板。混凝土建筑。...
王澍 虚构城市 Fictionalizing City 基本上,我们所讨论的“功能-结构”的方法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出自索绪尔开创的日内瓦学派的结构语言学,进而由雅克布逊等学者在音位学层面上建立了有影响的功能方法,在人类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电影研究、精神分析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等领域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另一个则是取自生物学的一份遗产。现代建筑中的功能主义带有明显的生物学功能主义的特征。前者把语言看做一种形式系统,一种分类学现象,并主张一种动力学的分析过程;后者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对分类学的价值有所认识。 无论是花园城市还是光辉城市,二种模式都从生物分类学转化过来。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柯布西耶的速写和草图中,动植物的写生数量之多,让人很难想象这是建筑研究,而如一位专业的生物学者,因为他的兴趣显然集中在分类系统方面。“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是柯布西埃最著名也最受争议的一个断言,广泛流传的解释把它和工业机器联系在一起,似乎缺乏人性的温情,但我以为这是误解。把它和生物系统联系起来,和一种不满足于经验概括、人为臆造与粗糙直觉而寻求一种更加抽象的体系化的空间组织概念联系在一起更加恰当。如果给光辉城市模式一个评断,那应该是:城市是住人机器。机器没有灵魂,这标志从主观偏见向种科学的客观认识的转变。 布洛克曼对现代生物学思想有过一段简洁概括: 有机生命似乎受到分类学价值的约束。于是有机体不再被看作有灵魂的生物,而被看作是一个对变化着的周围环境自动作出有目的的反应的适应系统。这一反应作用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持结构的内稳定态。其它的重要问题是,系统对影响的反应程度,组织防御的程度和以何种机制来维持稳定。这种思想方式似乎保证了内稳定态会被维持,虽然它只代表生命过程的一个模式。...
董豫赣. (2007). 文学将杀死建筑. 神话 抽象与具象 身体与控制 时间六像 落叶缤纷的事件...
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 中国古建筑二十讲 中国建筑图解词典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 穿墙透壁:剖视中国经典古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史.刘敦桢 中国古典园林史 江南园林志-童寯...